《中国乡村》的主要研究论题是清帝国统治者对乡村实施的社会控制体系和乡村居民对该控制体系的反应,以及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如何影响着双方的互动行为的方式与实际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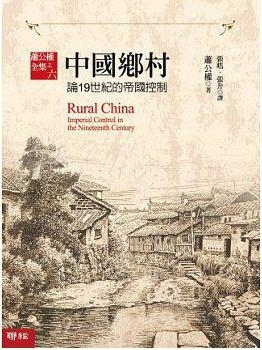
萧公权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以英文出版的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巨著《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终于有了中文译本(张皓、张升译,联经出版,2014年1月),确实如汪荣祖教授在该书的中译本弁言中所言,“中文世界里的不少读者渴望久矣”。汪文略述了萧先生当年撰写该书的缘起、出版经过,更指出中译本虽距原书出版有半个世纪之久,“但此书资料的丰富以及论断的谨慎与允当,仍极有参考价值”,并以人类学家施坚雅的名作《中国乡村市场与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得益于萧书之处颇多,绝非汉学家仅仅为人类学家提供资料而已”为例阐明其学术影响,所论甚是。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曾高度评价该书,认为它与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著作、瞿同祖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的研究著作共同为近代中国社会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见解(Reivew 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acific Reivew,Vol.36,No.1,Spring 1963,转见吴原元《略论美国汉学的成功之道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兰州学刊》2013年第1期)。另外,美国学者欧达伟(R. David Arkush)在其《中国民众思想史论——20世纪初期~1 949年华北地区的民间文献及其思想观念研究》(董晓萍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一书提出的问题是:“正统思想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农民的思想呢?”这正是萧公权在本书第六章重点研究的问题,他认为萧公权的研究很值得重视:萧公权通过研究清代乡村社会的资料,认为清政府大力在乡村推行“思想统治”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正统的礼教规范被地方的贪官污吏们歪曲了,清代乡学已经衰微、名存实亡,官方要借此控制民众的思想,其实是留下了一片“思想的真空地带”(第48-49页)。而欧达伟自己的研究论题则是以华北地区的秧歌、民间谚语等民俗资料为研究对象,“想从中了解,中国20世纪以来的革命转变在民众头脑中的转变是什么?为什么?它们的影响怎样?以及带来了什么结果?”(第116页)从中也可以看到萧公权《中国乡村》对其研究思路的影响。
《中国乡村》的主要研究论题是清帝国统治者对乡村实施的社会控制体系和乡村居民对该控制体系的反应,以及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如何影响着双方的互动行为的方式与实际效果。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乡村地区的组织”,描述村庄、市集与城镇以及基层行政组织的基本状貌与问题;第二编“乡村控制”,从作为治安监控的保甲体系、作为乡村税收的里甲体系、饥荒控制体系和作为思想控制的乡约等教化制度等四个方面进行全面论述;第三编“控制的效果”论述了乡村控制的效果、宗教与乡村控制、乡村对控制体系的反应等问题,最后一章“总结与后叙”把研究的视线从十九世纪延伸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农村的实践。作者对这种内容结构的说明是:“前面几章,尝试说明清代乡村控制体系的理论与实际,以及评估它对清政府的用处。在剩下的几章,将要追踪对乡村居民及其生活方式的控制的效果,并描述他们对控制的反应。希望这样能够更完整地显示乡村控制对帝国整体的影响,更准确地评价这种控制作为专制统治下维持政治稳定的工具所发挥的作用。”(第305页)实际上就是从帝国的控制与乡村居民的反应行为这两个方面研究专制统治如何维持农村的政治稳定。
萧先生在“序”中讲述了研究宗旨与所采取的方法,即以历史研究而非理论建构的方式,通过尽量具体、准确的描述,“描绘出相当清楚的图画,给读者留下准确的印象”;“换句话说,笔者所关心的是呈现出特定时间里实际存在的相关情况和过程,而不是普遍适用的一般观念或范围广泛的系统性组合。只要资料允许,笔者尽可能地从不同角度查阅、研究每组事实,也尽可能地放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至于萧氏的政治思想研究与这部乡村的帝国控制研究的关系,其内在的联系非常明显,甚至在全书开头第一句话就清楚地显示:“像帝制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界限相当清楚,他们的利益也背道而驰。”作者对这句话的注释是“韩非(卒于233BC)是第一位明确表述这个观点的中国政治思想家”(第3页)。在全书最后一章“总结与后叙”的开头,又重复了这句话的意思和这个注释(第591页)。更重要的是,该书的核心结论是:清朝的乡村控制体系是建立在统治者与农民根本利益对立的基础上,为确保政治稳定、使政权垂之久远而制定的一套由各种子系统所组成、各自具有特定功能的控制体系;乡村生活的每一个重要面向在理论上都置于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之下,帝制晚期的中国乡村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而作为帝国统治者的代理人,地方绅士广泛地被用来帮助实现对农村的控制,但政府又小心翼翼地对他们保持密切的监视:乡村社区中既有的组织或团体经常被用来作为控制的辅助工具,但又毫不犹豫地限制它们的活动或完全禁止(第592页)。
实际上,萧先生以其对中国政治的深刻研究和卓越洞察,几乎在这个控制体系的每一个子系统中都揭示出它们的政治目的与陷入的两难困境,而不言而喻的是与他对只有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格局下才能解决中国乡村的治理问题的思想观念相联系。例如关于建立地方粮仓做救荒机制,“清王朝统治者事实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把地方粮仓置于政府监督之下,地方的漠不关心和腐败,很快就会让它们失去效用;但是如果地方官员干预,原本关心它们的地方领袖,就会撒手不管,结(果)许许多多的不法行为就会出现”(第199页)。更精辟的是对帝国思想控制的分析:“思想控制的中心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士大夫变成无害的。然而,恰恰因为他们是被以特殊地位与特权来诱导,以符合规定的思想模式,因此他们无法发展出知识的热情或道德的力量。……换句话说,长期持续的思想控制,终结在士大夫道德和知识的萎缩;而清朝正是依靠这些士大夫来协助统治,并将思想控制延伸到辽阔领土上的遥远角落。追求思想安全就这样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清朝统治的道德基础最终被削弱了。”(第295页)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清政府通过科举制度与学校体系进行思想控制,以确保乡村地区的安全,并未取得显著成效”(第299页)。
更重要的是作者揭穿了这套控制体系的根本秘密:“整套复杂的乡村控制体系,是统治者设计出来的,目的是要把对权威的害怕灌输在人民的脑海里,养成他们接受现状的意愿,防止他们发展自立的能力一简言之,使他们在政治上无害、在思想上迟钝。这些制度并没有达成理论上应有的结果,但它们的长远作用,藉由历史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加强,有助于强化一般村民的特点,让他成为温顺的、缺乏自信的、无法自立的人。”(第488页)在全书将结束的时候,作者还谈到后来的人,“他们显然懂得专制统治的技术。他们所采用的控制方法,比清朝统治者所用的明显改进了,但基本目的及控制的根本原则基本是相同的:透过思想、经济和行政的控制,让现存政权永久长存”。
全书最后一句话:“我们希望,对19世纪中国乡村情况的研究,能够为解释最近的发展提供一个出发点。”对这句话的注释有两句话,第二句是:“我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推测,看来得到了一些证实。”此论使人想起农学家董时进的预言。
书后的“编辑室报告”讲述了对译稿进行编辑、校对、引用史料与专有名词的还原等过程中的艰难及处理方法,也颇有参考价值。但美中不足的是,目前书中的印刷错字、漏字仍然存在,祈望在再版时能改正过来。




